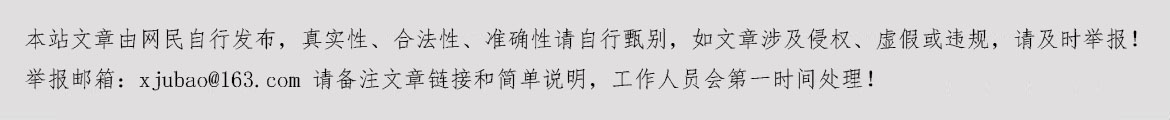走进冰雪地带:1998年那曲抗雪救灾纪事徐斌胜
1998年春节前夕,还是义务兵上士军衔在西藏军区某汽车团宣传股任新闻报道员的我,在深夜里接到让我随车队去那曲抗雪救灾的命令。股长李培荣特意给我拿来一件皮大衣和一个充电暖手宝,并特意嘱咐我,这次行动在无人区未知情况很多,一定要记录好宣传好这次救灾任务。
接到去藏北救灾的命令之前,我早已在报纸和电视上领略了大自然的残酷与无情,雪早已在我对它充满崇敬与神往的意境中猝然间变成了恶魔。天刚蒙蒙亮,我们满载三军将士和救援物资的车队风驰电掣冲出羊八井河沟的瞬间,面对冰铺雪裹的群山,寒冷在悄然间与恐怖和惊悸钻进了心间。
坐在三菱指挥车的后座上,时速100公里的车在冰雪中飞驰,发出“嚓、嚓、嚓”的声音和车厢里寂静的空间,使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慌,车在雪地里飞驰中突然颠簸着跃上一片白茫茫的雪野。刺眼的光芒顿时透过厚厚的玻璃直射我的双眼,慌忙中我急忙摸出了墨镜带上,路在银色的世界中剩下一条黑色的飘带。夜幕降临时分,白色的世界中突然闪烁着点点黄色的灯光。我们车队驶进了藏北重镇——那曲。
当我们的21台汽车似一条长龙穿过街道时,人们拍着双手迎接我们,随即爆发出吹叫声,车窗外、一声声“金珠玛米呀咕嘟”(解放军菩萨兵好)的呼喊声,传进了寂静的车厢里。我的心里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我们吃完了饭,在月光下开始给汽车上防滑链,加防冻液,为第二天奔赴聂荣、安多等重灾区做准备。
那曲,这片广阔的草原对我并不陌生,我早在几年前就在马丽华《藏北游历》里认识了这片充满诱惑的羌塘草原,在我印象中,这里草肥马壮,牛羊如云,有剽悍的草原汉子,有能歌善舞的牧女,可眼前的皑皑白雪和扑面而来刺骨的寒风,使我禁不住裹紧了身上的皮大衣,走进一片茫然而冰冷的世界中。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突然在睡梦中被人拉起。负责指挥这次任务的副政委刘辉,手里拿着我昨晚丢在车上的皮大衣正站在我床前。我以紧急集合的速度穿好衣服,罩上大衣,带上照相机和摄像机,夺门冲出房间。
我们被派往聂荣灾区,一共16台车,临行前,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杨晓渡,那曲地委书记杨骏等党政领导为我们每人戴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
为我们带路的是聂荣县县长江措拉姆和副县长加多。在他们焦急神色中,副政委刘辉命令车队全速前进,前面一条约两米多深的雪槽中忽隐忽现的冰路出现了,车轮在上面只转不走,在风雪的呼啸声中猛烈的跳着“迪斯科”。车队淹没在积雪中,在冰路上如蜗牛般缓缓而行。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终于爬上了海拔5200米的查桑拉山,山上风雪交加,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冰路上有一层厚厚的积雪,满载救灾物资的汽车无法驶过,几十名官兵裹着大衣,扎着腰带,手持铁锹,在雪地里一下一下的敲打着坚硬的冰层,然而一切无济于事。不知什么时候,雪地里突然钻出二十多个群众,铲冰拖雪,连推带拉帮我们把六台车推过了山顶,虽然我们无法用语言交谈,但从他们那欢愉的神情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子弟兵的那份诚挚情感。
握手告别了这些淳朴的草原乡亲,温暖不由得在心中涌动,久久不能平静。透过车窗,路边老鹰、兔子、牦牛、黄羊等动物一具具尸体在白色中显得阴森而凄惨,此时,在这被文人赋予诗意与美感,像征纯洁的白色面前,一切生命是显得这样脆弱。给人寒冷、饥饿、无奈、绝望的感觉。马丽华《藏北游历》的那份神秘与惬意在心中荡然无存。
路边偶尔在风雪中闪出一顶冒着青烟的帐篷。在荒凉中让人不禁在这被生物学家断言为所谓的生命禁区里感受到生命的旺盛与活力。在卓嘎老阿妈的帐篷前,我们车队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我与卓嘎老人在他羊粪炉边亲切地交谈起来,带路的达瓦师傅当我们的翻译。卓嘎老阿妈说,这是他记事以来下得最大的一次雪,可是有共产党、有金珠玛米也没什么可怕的,虽然她家冻死了一些牛羊,但在这种灾害中,那也算不了什么。现在家中只有她和孙女仓吉,儿子和儿媳都去参加民兵抗灾救灾突击队了,经常有“本布拉”给他送东西来。临行前,我把一副墨镜和一双皮手套送给了卓嘎老阿妈,她给我戴上一条洁白的哈达,握着我的双手,摇着转经桶,诵颂着经为我祈祷平安。在这人喻为“生命禁区”的雪原里我体会到了世间最神圣的情感与人情。这里虽然天寒地冻,没有鸟语花香,没有现代文明的喧嚣却有世间最可贵的真、善、美。我不禁为曾被推崇为一个时代伟大探险家的瑞典人斯文赫定自信宣称:“海拔4500米以上雪域高原是生命禁区,人将永远无法定居生存”的谬论而愤慨,如果他知道,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还居住着一个有悠久历史、有灿烂文化的民族,那他将会羞愧闭嘴。
车队在一个冰河上东拐西弯了10公里后开始进入一片峡谷中,四周群山间硕大的石头波纹显现而立,可以使人感受到亿万年前特提斯古海的浩淼。视线中终于出现了一排低矮的房子,这是聂荣县城。官兵们卸下煤炭柴禾、糟粑、绵被、药品、饲料等物资之后,启动汽车准备返回,许多群众手里捧着哈达端着酥油茶哭喊着,不让官兵离去。
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在雪山的褶皱里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在寂静与苍茫中,只听到发动机的引掣声。四周的牧民涉过没膝的积雪为我们送行,我们一路鸣着喇叭告别这里如雪山般雄壮的牧人走进灰白色的夜幕中。四周的雪峰像一柄柄利剑,在夜色中闪耀着冷峻的寒光。我们车队在令人眩目的雪地里折腾了3个多小时,终于在雪海中走投无路,退不能、进不是。汽车在积雪中挣扎着,最后反而越陷越深。专业军士李良贤想出一个办法把棕垫和被子绑在车轮上防滑,可最后还是无法走出“绝境”。就在这时,驻藏某山地旅政委刘庭华率领的救灾车队也到达山顶,汽车兵出身的他最先脱下皮大衣垫在车轮下。并亲自驾驶车辆组织脱险,两支救灾部队顶着零下38摄氏度的严寒,拓冰挖雪,用皮大衣铺一条通道,在充满死亡的深夜雪路里寻找生的希望。此时的我心中没有任何恐惧。一切是那样坦然。凌晨4点30分我们终于把第一辆车弄出了“绝境”,用钢丝绳一台一台把车拖到冰路上。在翻山口时,我们又一次被风雪耍弄,再一次迷路,这时只见远处有十几个手电光在银灰的夜幕中朝我们闪耀,一直翻过查桑拉山。原来是在查桑拉山上帮我们推车的藏胞怕我们迷路,一直在山上等候我们。
在这“生命禁区”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与活力,在这“冰雪地带”我领略到了这里藏胞的淳朴与善良,在这高山之巅,蓝天之下的土地上,人的情感和灵魂像雪山一样晶莹,像冰峰一样洁净。这里的人民是强劲的风和自由的云,他们就是高原,就是一座座巍峨屹立的雪山冰峰。他们的意志与强悍一定能战胜灾难,继续悲壮地在羌塘草原繁衍生息。
后来这次抗雪救灾评功评奖,我荣立二等功。
左1为作者,左2宣传干事马玉荣,左3解放军报记者杨彪,左4战旗报记者刘励华,左5新华社记者刘永华,在救灾途中合影。图片由李伟明提供
(本文图片由原西藏军区后勤部专业军士李伟明提供)
作者简介:
徐斌胜:云南大理剑川县人,白族。1993年12入伍,2014年1月退伍。曾在西藏军区驻江孜某仓库,汽车十六团政治处,西藏军区后勤政治部服役,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西藏日报》,中央电视台,西藏电视台等媒体发表作品2000多篇(条)并多次获奖,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六次。
作者:徐斌胜